新年伊始,记者专题采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南方画院院长陈晓明先生。画家侃侃纵论,妙语连珠,颇有见地。
记者:作为当代国画名家作品个案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发行你的新画集引起美术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你是怎样看待自己这种“山川苍莽”情结?
陈:2002年广东美术馆作为当代水墨研究课题,为我主编出版山水画集。时任馆长的王璜生在前言中首次提出:陈晓明作品“力图表现山川苍莽”的看法。西部山水苍莽而富于生命力。西部山水的欢乐、悲伤、细语、呼喊,无处不显示着我们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民族的浩荡胸怀和博大精深的灵魂。
“山川苍莽”对我而言,无论对美的发现抑或是对美的创造,既是“天人合一”的一种缘份,也是人生一种美好的追求。“山川苍莽”是我的笔墨,是源于大自然体验的“胸中丘壑”,也是我创作的一种符号。
记者:大家感兴趣,作为南方画家你为何选择西部山水作为主载体?你的作品是否也存在对南方山水的感受?
陈:这涉及到审美意识的认同和审美观的差异。作为南方画家,长期深受岭南文化的浸淫和岭南山水的感染,我对这方水土有自己的情感寄托。如云涌的飘渺、山川的空灵、山泉的婉约,雪松的秀雅……,这些都包含着我对南方山水的情怀。我力图画面大气势的同时,注意山体皴檫、浑染、上色等各个造型环节的情感支配,若隐若现在云飘山动的氛围中给读者一份南方湿润和阳光的感觉。
我是学中国文学的,骨子里多少有些人文情怀。在文学上,我比较喜欢苏东坡“大江东去”一类的豪迈风格。因此,在国画创作上,我采取大开大合的构图形式,注重大气势整体的把握。2008年,我从成都乘飞机到尼泊尔采风,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我从高空俯瞰这苍苍莽莽的千秋雪域,再次被视觉中的大山川震撼。感觉令我更坚定选择西部山水作为创作主载体是可为的。尽管我的作品缺少一草一木、一屋一石的细节描绘,但我却把 感觉中的雄奇和苍莽气息传递给广大读者共享。这也是我的中国山水画特色。
载体的选择与地域文化并不存在直接关系。比如徐悲鸿遍游世界,只创新“一匹马”;齐白石阅尽京城风物,却选择一只经典的“虾”。事实上,视觉和感觉是不同的概念。视觉具象一般是真山真水;而感觉只是人们的意识反映,可以是抽象的、变形的,甚至是后时代的幻觉。祖国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创作载体。关键是应该有感而发,谁发现美并为之激动,为之能用笔墨表达心灵的真实感受,谁就有创作的话语权。有人认为我的“山川苍莽”只是对西部山水的“一见钟情”。这有误解。即使是“一见钟情”,也未必无情无缘无爱。相反,一生在熟悉的环境中,有时也会产生熟视无睹的无柰和视觉疲劳。因此,我们要共同努力培养起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以欣赏的心态看待多层次多元化的审美新格局。
记者:一讲中国画,通常会以“传统”去评头评尾,有人认为你的中国画是传统文人画的另类,你对此有何见解?
陈:我对“传统”态度是尊重和反省。“传统”一词实际上比较空泛,据考还是从日本国传入的。有些人喜欢动辄以“传统”忽攸人,可自己对“传统”究竟有多少正视?以中国山水画而言,宋元山水画较为典雅大气,并初步形成专业画种。古代中国画处在一种比较自我的戏墨弄墨状态,特别是泛指旧文人画的明清国画,把玩水墨只是旧文人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古代画家受视觉局限,观察自然是平视的。因此,宋元明清留下的山水画,其构图多数采取直观的“三远”透视造景。而当代人可借助现代交通登高远眺,也可以乘坐飞机直上云宵俯瞰天地山川,无论是创作思路或体验自然的视觉都得到深度开拓,可以获得俯视角、全景色的创作效果。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被人们视为最具传统特色的文房四宝,其质量和用法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认为断不能用千百年前的审美意识评判和衡量当代中国画的价值。无论是创作意识或笔墨工夫,当代中国画的进步已成历史事实。
作为当代国画家,我只能在尊重“传统”笔墨形式上发挥当代艺术精神,画自己的画,画给当代人欣赏。我开拓的“俯视角、全景色、暖色调”的创作路子仍在变化中;我希望自己在创作中有更美好的发现。对我的画作,感觉到什么并不要紧,能让人视觉舒服,多看几眼就满足了。至于是否另类?不是我关注的,让后人去评价为好。
记者:经历几十年创作生涯,你认为自己哪些作品最具代表性?如何看待作品学术性和市场价值?
陈:我真正能画画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倦鸟知归》;九十年代的《岭南潮》;近年的《昆仑之秋》;《梅里圣域》;《天山人家》等,读者如有兴趣可多看几眼。
关于作品学术性和市场价值,这问题很尖锐,是当代画家面临的痛苦思考。作品学术性的讨论由来已久,有较统一的价值认同;而对作品市场价值界定至今较为模糊。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不可能等同,但各自价值是可论、可评、可判的。随着社会变革,艺术市场的需求以及当代审美观的多元化,对艺术家构成新的创作压力。寻找符合艺术家良知的个性创作而同时又能融入艺术市场的平衡点,这是当代艺术家面临集体性的阵痛。以我为言,“山川苍莽”是我的艺术选择,但并非是最后的选择。无论我的创作形式如何的变化,终极必须服从一个艺术家的良知。保持学术追求,同时能适应审美意识的变化,我正在努力探索这新课题。
记者:最后想请你谈谈今后创作打算或计划?
陈:坦率的讲,我没有什么计划。大道自然,一切取决于有感而发。从事艺术,本身是很孤寂和个性化的 。最近我同许多朋友讲,守望乡村、致虚守静是我的生活现状,也是我的艺术状态。几十年走南串北体验生活,应该静下来梳理思路了。我仍有许多感受要述说,创作欲望似乎正处在一个厚积突发的一个节点,自信今后能创作出更好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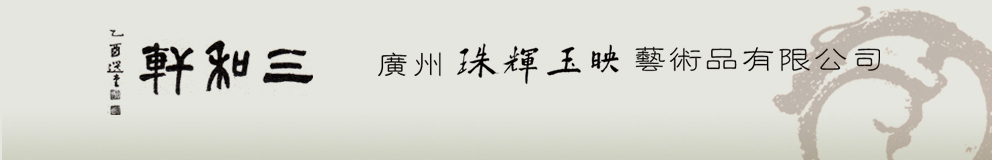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