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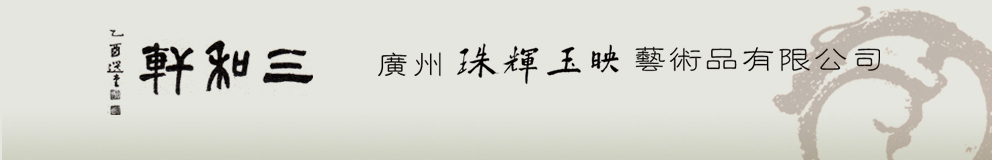
粤东饶平县的山里有个渔村镇,习称“惠村”。惠村有个村子叫“金背塘”。
也许在其他人眼里,金背塘只是一个普通的毫不起眼的小山村,但在我和杨培江、肖庆书、陆晓翰等画友看来,它又不仅仅是个小山村,因为我们20多来年的青春岁月和在“艺术界”浮沉挣扎的历程,跟这个小地方密切相关。在我们的惠村写生史上,金背塘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圣地”,这一说法,毫不夸张。
金背塘座落在惠村镇旁边的一个山旮旯里,没有熟人带路的话你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马蹄形的山窝,座北朝南,横纵之间不过100米见方,依山建有许多房屋,村民们世世代代在此生息,繁子衍孙。鼎盛时期,村里住有老老少少百多口人,鸡犬之声相闻。孩子们不用读书时,就在环绕村子的山路上追逐打闹,一路吼着从电视上学来的流行歌曲。每到做饭时,家家户户炊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稻草燃烧的味道,我们每次在山上画着速写,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想起来——又到吃饭时间了,这时,肚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响起了咕噜!
金背塘很美,山上尽是果树,有桃、李、杨梅、杨桃,每到4月杨梅成熟时节,满山红遍;杨桃果实一枝一大串,随你采摘——山里人纯朴好客,进山的人口渴了摘些果子吃,他们是乐意的。金背塘人丁很旺,尽管是山村,但不管一草一木,都散发出勃勃生机,日出日落间,小伙们越发虎虎有生气,小胡须噌噌疯长;小姑娘们原本单薄的身段则日见丰满,有如村里到处都有的木瓜树,滚圆滚圆的,青脆欲滴。她们不时穿梭在屋前树后,红衣绿带闪烁其间,一声声“老师又来啦”叫人温暖,也令原本沉闷的山村平添了些许温馨可人的青春气息。
山窝的底部本来有一块比较完整的开阔地,有点像乡场的模样,乡亲们在边上种些木瓜、南瓜等,充作菜蔬,而作为我们画画佬,这些却无疑就是大可入画之物!后来,这块空地渐渐被蚕食;再后来,在培江的鼓动下,干脆在硕果仅存的一小块空地上建起了一间小房子,堆放写生物件,并且在屋外搭起一个凉棚,从此,大家去了也有个喝茶聊天的场所,只可惜,乡场从此消失殆尽了!我早年有一幅画叫《紫气东来》的,大体就是画它原来的样子,有时看着这张画,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凉棚的边上是好青年红勇的家,他有个妹妹叫红凤,长大以后出去打工了。他们的父亲庭锦叔为人谦细善良,话语不多,然而令人觉得亲切无比,经常招呼我们:“老师来家里喝碗粥啦”!连我的婚姻大事,他也时时记在心上,每逢我进村写生,他总是一边泡茶,一边语重心长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劝我要早点成家。庭锦叔已于几年前过世,如今在金背塘再也没有人陪我们泡功夫茶了,也没有人煮好鸡粥叫我们下山吃饭了!在红勇家的对面山坡,是“耳聋伯”的家。耳聋伯年轻时是个卖豆腐的,其时是否耳背不得而知。据说文革时村里民兵动辄没收东西,“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一天耳聋伯托着一板豆腐到镇上叫卖,被民兵抓个正着,尽数没收,他还屁颠屁颠跟在人家后边问:“是不是全买了,是不是全买了”?听来好笑,其实令人心酸!耳聋伯并没有跟上全民奔小康的步伐,晚景令人唏嘘,儿女们独立出去住了,他和老伴靠种些果树过活,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地里辛苦劳作。耳聋伯和老伴关系不好,老两口时常吵架,吵的还很难听。我和培江偶尔给他些零花钱,或到肉摊上割几斤猪肉送给他,他都是再三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去才收下。在耳聋伯家的下一梯级便是晓燕她家。晓燕是金背塘的女孩中我们这些画家最熟悉的,在我们20年来时断时续的眼光见证中,晓燕由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黄毛丫头再变成一个青春少女,最后终于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出门打工并最终远嫁外乡,这似乎预示着金背塘情结的必将终结。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晓燕有多么漂亮,而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不知不觉把她作为善良、淳朴、可爱的山乡姑娘的典型代表来看待,尤其在我们早年的金背塘写生史上,晓燕活泼的身影、在树丛后边传来的清脆的笑声、家里的羊不幸在树上吊死后她的悲伤神情等等,都已经变成了我们对金背塘的记忆的一个重要的、挥之不去的内容,以至于后来听到了关于她的一些不太令人开心的消息,大家不禁都随之不开心起来,尽管我们清楚:对于金背塘以及它的村民们来说,我们这帮不时进来写生的“老师”,只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外乡人,我们对乡民们的喜怒哀乐,对农村生活的艰难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一些片断,然而他们总是以友善之心把我们看作自己人。尤其是培江,因为带学生进去的次数较多,早已经达至无人不识的地步。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把回金背塘当成回家,如果因为生计的关系太长时间没进去,就会觉得怅然若失。
出了山窝往西边拐进去,是一片开阔的梨树林,绿草如茵,阳光从山上树梢撒下来,刹是好看。我每次进去画速写,在那里坐上一会,享受山林的宁静和惬意……
——可惜,以上描述的,是多年以前的金背塘。如今的金背塘已经彻底衰落了,整个村庄除了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留守”之外,空无一人,年轻人都陆续到外面打工或读书,成家的就搬到村外的新居去。随着老年人的陆续离去、人烟的日渐减少,金背塘的房屋风化坍塌,杂草丛生,村庄的轮廓日渐模糊,我甚至不敢想象十年后的金背塘会是什么样子……
以20多年的时光见证一个写生基地的衰败,着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这个曾经美丽的小山村赋予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画家以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她的倩影已经永久地定格在我们的作品中;况且,这块狭小的土地养育了许多年轻的生命,他们已经像种子一样撒播到更大的天地中,去生根,去发芽,金背塘的生命、地气和福气,业已传承到她的后代身上。想到这,我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2003年初稿,2008年11月完稿于广州紫篁小筑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