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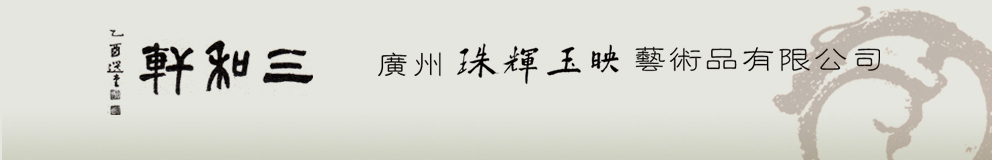
接触广东画院专业画家陈映欣之前,曾听人说他的策展做得好,文章也写得珠圆玉润,近日,记者专程拜访了他。作为一位画家,陈映欣的个人经历颇为曲折丰富,曾经从事过陶瓷设计、室内设计、广东美术馆策展人等许多工作,调进广东画院以后,他才有比较多的时间用在画画上面。陈映欣的美术视界融汇传统笔墨与空间创意,取得了绘画、理论、策划三个行业的和谐共振。记者在他的画室观摩他的一幅幅为即将到来的个展作准备的新作,采访中发现他本人也有了三个“岁月年轮”,即从早年的那种十分狂放的“野味”绘画,转到“野味”够了之后的“中和笔墨”,另外由于他本人的设计与策划渊源,在他的画面呈现上瓦解了一种“实验性空间”,亮滋滋地自成风骨。
从“野气”到“平乱的秩序”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您画心渐浓,画意潜涌,创作状态也相当的旺盛,回首您之前的绘画探索,大家都说您的“野气”渐敛,“空间”渐出,而我知道您1993年的获奖名画《紫气东来》,很有一种让人眉头一挑的画面解构,这张是不是您最“野”的画?
陈映欣(以下简称陈):也不能说这张画就是最“野”,不过它见证了我那时刚从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野”气十足的年代。《紫气东来》一出炉,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不顾传统的东西,平铺着一种“山村紫调”,画面没有空间对比,要的完全是主观印象,专家们抬眼问道:想不到现在的青年人竟敢这样来画。不过它的获奖也证明这幅画在当时来说还是有所突破的,尤其在色彩运用方面。它具有某些拓宽山水画视野的价值。
记:接下来您就开始“野气”内敛,总体体现的是一种“走出秩序”到“重新回归秩序”的过程,中间有哪些分水岭般的画作?
陈:1999年我参加九届全国美展的作品《归去来兮》,就显得文雅一些,不那么“冲”了,通过温和的色彩来淡化笔墨,取得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野”中带“文”的效果。在2005年,我创作了《瑶山高》,许多画友评价这是我当年最好的一张画作,它在我近年的创作中具有一种“转折”意义。当时我也觉得自己“野”够了,率性的东西过满则溢,于是就想带着“野”性思维来取得对传统的一种螺旋式回归和上升。所以这张画我用“中和了的野气”,吸引了传统山水画中的构图方正、平稳、层次感、景深氛围等特征,笔墨和渲染比较从容,让画面的色彩和用笔显得张驰得体,开始没有“野”得那么过分。这件作品我自己觉得比较沉实、大气。
记:那现在您的风格探索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陈:我觉得画家应该有所坚持,现在我还在营造着自己特有的“野气”空间,但心态已经比较平稳了,知道如何直面传统笔墨与现代实验性画面的关系。我有幅很满意的新作叫《黔地寒秋图》,是贵州写生的印象之作。画面中枯干的线条结合水份淋漓的渲染,以求得一种既苍劲又润泽的效果,较好地表现出山地辽阔多姿的气势。这幅画就“野”得很有“秩序”。刘斯奋院长评价我的画谓之“乱中出空灵,平中见空间”,就是说我的画面“乱”,但“境界很安静”;画面“平”,但平中又透出笔墨“层次”;美术大师林墉评价我的画时说:“色又色,墨非墨,乱来正是真来”。我自己倒觉得,以前我的“平”和“乱”是“走出秩序”的,现在回归到了一种“提升了的”秩序,从而形成了我的画面“平乱的秩序”的风格。
“游心游意”出“平乱”
记:大家对您在绘画题材上的定性就是:您是“一个山水画家,兼画墨荷”,然而您的生活却是“游态毕露”,之前的工作做过陶艺设计、美术策展等,有好长一段时间“游离”于主流美术界之外,您自己也说自己的画“游态”毕露,很多是“率性”而为,究竟你画面上的“平乱”是怎样炼成的?
陈:石涛所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搜”字的潜台词就是“游”,通过一种“泛目的性”的行走来获得一种山水形制的概念和印象。我在童年时就陶情于家乡村子前后的山山水水,其后因生活、求学换过几个地方,毕业后又四处奔波,生活状态一直是处在一种漂移的情景之中,于是我产生了“游心”和“游意”,其中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生活遭际让我在“游”历中求“安”,而“游”的心态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于是我的画面就多了一种驿动的、开放的心境,点化的是“飘过岁月和他乡”的绘画哲学,心境所致自然抒发,不一定要刻意框住自己的面貌做什么系列画,却保持自己的中心语言:气韵和空间。我想我现在的初步风骨就是山村画中的自然自适、自然、自在、无畏的心态所“平乱”地泼墨。
记:您以画山村画闻名,您的同学和朋友、广州画院的专业画家李东伟也以“中国乡村系列”形成他近来的风貌。我曾问过李东伟,他对您的画评起来也是很肯定的“率性”出“空间”。可您似乎对于作“系列画”不太赞同,这是为什么?难道一个画家积聚之后,不应该找到一个大致的面貌聚拢一批主题作品吗?
陈:李东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画家,他很早地就开始框定自己的风格,然后开始套出一批批、一系列的主题作品。艺术手法本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方式”的不同而已,我并非不赞同画家作“系列画”,但我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创作方式。我觉得当代的画家急于寻找自己面貌和风格的太多了,他们往往创作出一系列的同种风格的画,像明星频频露场一样“混个脸熟”,这一方面确实会让大家对他很快有个定性认识,然而另一方面又会出现面貌的重复,很多率性的东西或者某时某刻的“胸臆”于是是被“框架”套死,表达不出来,导致失之于生动。创作的“商标化”是当下画坛的时髦现象,我最近在一篇理论文章中也谈到这一点。其实风格不一定要靠“系列画”来定性,我总觉得,艺术的最高级状态,应该在乎“有想法”和“没想法”之间,在乎“有所求”和“无所求”之间,一个艺术家风格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画家个人所有的作品就是一个大系列,这个大系列迟早会自有风范,那就是艺术家本人长期修炼而来的笔墨特点和随之自然流露的艺术气质,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实验性空间”其实是“我”的空间
记:您多次提到自己的画面“平”中出“空间”,而且还毫无讳意地把这种空间称为“实验性空间”,以形成您独树一帜的地方,能否解读一下,让大家共赏?
陈:大凡山水画,总是采取近景实、远景虚的结构手法,以达和自然景物重合的那种层次感。然而我自己的画并不拘泥于近实远虚,有时讲求把远近拉在一起,以同样的“实”景让整个画面“平”起来,层次开始模糊;有时又讲求近虚远实,或者近虚中实远虚,不停地排列组合,以在画面上形成如同镜头一般的“视觉凝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中国的山水观带有极为强烈的哲学意味和生命意识,这一点倒是和西方的风景画在整个审美逻辑和美学追求上有着质的区别。而所谓的哲学意味和生命意识,就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镜头凝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审美眼光形成不同的画面观感,并不一定近的就看得实,远的就看得虚,而应该对整个画面采取“俯瞰”式的观照,所以,焦点就是实景所在。而这个焦点,往往就是艺术家结合自己的意韵和情感,所要表达的,也是他所希望观画者聚焦的,这个焦点不一定要在远或近,有可能在中间,有可能在侧面。
记:那您这种画法,是不是山水画中所采用的“散点透视”法?为什么这叫做“实验性空间”呢,是不是您的设计、策划思想在画面上作怪?
陈:散点透视是通过时空的不断切换和嫁接,利用“倒叙”、“插叙”等手法来打破原来的空间逻辑,从而增加了画面空间的进出路径,读者要不断地转换角度和视点,才能真正进入到其中的复式组合空间里。但我的空间还有所不同,我讲求“古典空间”、“想象空间”和“经验空间”的混合体。在画面处理上大量地利用林木植株置于前景,间留有隐约的路径或是溪流泉练逶迤而出,衔接了画里空间和画外空间的逻辑关系,使人在进入的时候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空间导向;排比式的树木俯仰穿插、纵横交错,处理得密密匝匝,形成画面上的视觉主体,然后通过云雾水气的处理形成了一个纵深曲折的空间,再利用一些山野间村舍亭阁的分隔,交代出空间的起承转合,交代出后延空间的深度走向,最后以远山设成屏障,交代了一个空间的“暂停”。这是我比较惯用的手法,通过山水之间复杂多变的空间,来表达“景小象大”的感觉。可能我的思维还与我曾经的设计、策划工作有关,我做过前卫的、实验性的美术展览策划,转移到我的画作中,就成了姿态问题。我喜欢这种姿态。我不以景物的自然空间为基,却喜欢“实验性空间”,有着不拘一格的焦点,这其实是“我”的空间,是我对于自然山水的情感在画面上的呈现。我觉得表现“空灵”和“气势”,跟山水的远近并无多大关系,我很少画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水,而更喜欢通过小山水、多空间,得到一种大气度。
(发表于2007年6月1日《广州日报》,记者陈志凌)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