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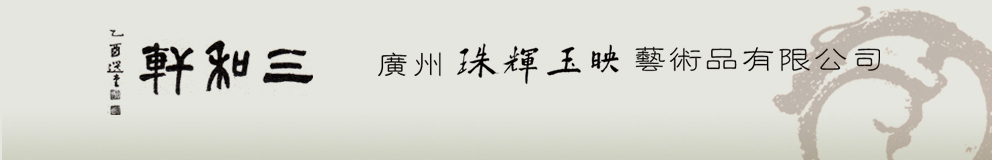
作者:孙晓枫
“林墉”这个概念是既单纯而又复杂的。说单纯,是指林墉一直守住艺术家兼作家的身份,靠两支笔(画笔和文笔)立世,不喜攀龙附凤,不喜交际,如其所说的“良师益友不过十人,从不串门、不拜年,除了办事聊天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画画和写文章”;说复杂,有多方面的意思,大概是,其一,在林墉个人身上聚焦了太多的赞誉和非议;其二,林墉在期望单纯中却又身不由己地陷入世俗场景的凡尘俗事和口舌纠葛之中。这一点使我们联想到他的文章:时而是清澈见底的对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对大自然以至小动物的脉脉温情,读之令人动容;时而却是对某些人情世态的辛辣讽刺,其不留情面和锐利言辞令人震栗;其三,林墉自70年代初的巨幅历史画到90年代末病后作品等几个时段的创作之间在创作动机和美学趣味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霸悍与恣丽”(王璜生语)、东方与西方、神圣与荒诞、严肃与调侃、哲理与村言、精细与狂放等等形而上或形而下的逆反概念,都悉数调和在他这二、三十年的作品里,既混杂而又脉络分明;其四,林墉的高度自信与面对超出自身所能感知和操控范围的社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形成的外力影响时,他的超乎常人的感知智慧与自我平衡能力。对以上问题作深入的学术探讨,可以使我们领略一位艺术家的个性风采以及明了某个特殊个案对于艺术研究的启示价值。这寄望于更多研究者的切入,笔者在此只是以浅陋的学识和对林墉有限的了解谈谈个人的所思所想。
艺术之于社会,谈不上必不可少;艺术家之于社会,更谈不上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纸笔之中体现自身价值和尊严,这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宿命,这一点林墉是极其清楚的,因此,他自称为“手艺人”,也由此,他在某个前提下建立了高度的自信,正如他言谈及文章的字里行间所表露的,他一直对自己的绘画能力颇为自得,并且“老早就计划好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无论这句话是出于成功者“桑麻话当年”的自许,还是青年时代的林墉确实已经未卜先知地预见到自己日后的成就,以及这个过程中与社会舆论之间必然产生的口水纠葛,于是预先作好了应战的准备,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其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历程作一次完整的回放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林墉的确是一位具备清醒预测本领和自律能力的艺术家。而且,在长期作为广东主流美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身份的特定圭臬之下,他一直都能够在一个有限的体制空间里游刃有余地展现自己的各项才能,并且总能找到自身艺术个性与瞬息万变的学术风云之间的某个契合点或对比点。这使他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人物。而且,他每个阶段的创作都具备清晰的面目和审美指向性,这在中外美术家中是甚为少见的。在笔者近两年与林墉的几次长谈中,他屡次谈及早年那批使他“标青”的巨幅历史画,可谓其情切切。我看得出这不是简单的所谓“老年人的记忆力总是出奇的好”(鲁迅小说句),而是他确实曾经对这批画投入了最深切的感情和激情,并且在这种近乎宗教膜拜的虔诚修为中渡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些作品,寄托了他青春时期对某种信念的激越情怀。无疑,它们在客观上成就了名人“林墉”,也成了新中国艺术史上讴歌土地革命的重要经典作品。但它们在延续自身生命、履行自身“责职”的同时,留给始作俑者的已经是另外一种心境和慨叹:“……后来,很不容易地明白了历史只不过是人写的东西而已,有些历史画只是以真实的画面去重复不一定是真实的别人写的东西,就很茫然,并也因此不敢随便画历史了,而竟也就到了无力画大画的年限!真可惜。……”(《马跑着,那是我》)这番话,说是对历史应有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感也罢,对政治风潮的荒诞终于有所认识也罢,对青春不再的感慨也罢,然而正是这个过程使林墉快速地成熟起来。抛开作品的政治因素,它至少第一,使林墉在美术界站稳了脚跟,第二,使林墉完成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画家的必要技术准备,庞大的场景和众多的各式人物无形中迫使林墉进行一次技法的大操练。第三,使林墉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巨大画幅——在现代艺坛中,能否制作盈丈大画是对一个画家的考验之一。第四点尤为重要:它们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令林墉获得决定性的自信,并在日后的岁月中保持这种自信带给他的从容和自我称量的天平。当然,林墉在言谈中也曾抱怨这批画未能获得美术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宣传,但这反过来似乎证实了我上面的推想并非臆断——林墉本人对这批大画有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令他至今难以释怀,其中有自傲,有失落,也有自嘲,但有一点是从未被岁月洗刷掉的,那就是他从来都以这批作品为荣。事实上,林墉对这些画的偏爱一点也不过份,因为,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度量,它们的水准仍然是相当高的,这点自不待言。在此我关心的倒不是题材、构图、笔墨等常规绘画因素,而是林墉在创作过种中全力以赴的投入和“为了效果不择手段”(《马跑着,那是我》)、“不论东西”的果敢和开阔的思路。笔者无缘拜读林墉学生时代的课堂习作,但经由这批画,我俨然已经和青年时代的林墉打了个照脸,并惊异于他的才气、锐气和野心——笔者曾经留意过林墉早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主人公总是意气风发、锐气十足,嘴唇表情丰富,一副时刻准备与人论辨的架式,这是否预示着他后来将成为广东画坛的风云人物、口舌之争的聚焦点,不敢妄测。我们知晓的是,林墉很早就坚定了日后成为一个大画家的信念,并为此有针对性地苦练各种“招式”,据他自己描述:“在教室坐着,临着一叠叠画,读着一本本书。为了描一个鼻子,可以废去十多张纸,为了咬通一个字,必须翻查几本书。……我从很早起,就从工匠师傅那儿秉承了勤快的手脚——不精熟,怎叫艺?一直到今天,我仍把制作的精熟当作标尺之一。我绝不相信热情和祝愿就可造就艺术。”(《马跑着,那是我》)对此,笔者除了感慨林墉学习目的的明确和刻苦的自学精神之外,更强烈地是感受到林墉对 “技艺”一词的独特见解,并恍然大悟为什么林墉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对女性肖像,女性人体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人物肖像特别是女性肖像、女性人体是林墉最为人熟知,为他争得最大观众群,同时也使他引人诟病的“福地”和“祸水”。对大众和专业圈仅仅关注他的“福地”而淡忘了他的历史画,林墉其实是颇感无奈的,但若说他自己不看重这批“美人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林墉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不时为自己的女性题材作品辩护,就是明证。据我推测,林墉对女性题材如此专注的原因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源自他始于儿时的对女性的依恋和仰慕:“我一直生活在祖母、母亲、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护之下,童年总泛着女性的柔光……我更易感觉到女性的优秀处,而欠缺了真正男性伟美的感觉。说真的,时至今日,我内心中不乏众多美好的女性,而偏偏一个男性的伟岸也没有”(《甲戍答客问》),其实,仰慕女性本是男性的“通病”,林墉只是表现得比较强烈而已,这是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一种解释,至于艺术上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得回溯到林墉对技艺的热爱上。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女性是美的象征,尤其女人体令人炫目的质感和曲线,汇集了天地之间美的法则和感觉在内,在它身上汇聚了具象美和抽象美的所有语言。这对痴迷于女性美和技法美的林墉来说,无疑是一片理想的“试验田”。况且,要以准确的感觉和线条抓住那摄人魂魄的动人瞬间,确实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林墉认为,技艺的精熟可以达至某种境界,技艺是把“境界”可视化的唯一手段,技艺未精而妄谈“境界”,无异于睁眼说瞎话。于是,林墉为此背上盛名与“骂名”,便成了无可避免的事了,对此,林墉的恼火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自己的画,是画给俗人看的,而有人不这么想,那很好……,极雅的人,大可不必来救我,我倒相信,时光会锤炼烧锻我的画,但相信并不至于全成灰烬。”(《甲戍答客问》)捍卫阵地的宣言可谓掷地有声。按照艺术原则来讲,其实并无手法上的熟优熟劣,更无所谓“写实”就低级,“精细”便非学术一说。至于某些画家和理论家,将林墉的人物画作为质疑南方有无“艺术”,有无“博大”的口实,不能说浅薄,至少应该说是偏见,起码折射了所谓“中原文化”对于“珠江文化”的不屑一顾的“正统”心态。此种情状,正如李伟铭君在一篇文章中所形象比喻的:“……他所选择的绘画母题中最稳定的因素还是那种具有典型南方特征的年青女性形象。尽管我们很难断定后者比那些拎着烟袋在墙根田头晒太阳的北方老农形象更好或更坏,但是,在这个似乎人人都熟谙“哲理”并善于“艰深”的时代,林墉笔下那种带有抒情自然主义意味的女性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天真、漂亮而难逃“浅薄”、“俗气”之讥“。(《林墉中国画人物写生精选》序)而在广东本土,后起的一些艺术青年(包括林墉的美院校友)则将其视为“庸俗”的典型和导致广东美术为外界所诟病的“害群之马”,甚至发展至以在课室“批判”林墉作为与“俗气”划清界限的“决心书”(尽管他们在心底里对被批判对象的绘画才能佩服之至)。其实,这也难怪青年们,当其时,王鲁湘等撰稿的电视系列片《河殇》,还有《黄土地》、《红高梁》等西部电影正在全国各地热映,而《走向未来》等召唤性丛书和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把美术学院的青年学生们鼓动成了半真半假的“哲学家”。对于向往“博大”、“深沉”的“哲学家”们来说,“林墉”之流无疑是最好的活靶子。笔者无意于否定当年的这股思潮,我觉得引人深思的倒是:何以把林墉作为“唯美”的代表?仅仅因为他画了一批好看的“美人头”?何以把他作为缺乏“学术”的代表?仅仅因为他表现的是南国水乡的村姑少女?当然,这些问题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我只是觉得,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外界一直都在按自以为是的牌理揣测、评价着林墉的牌路,只可惜,林墉一直都不屑于理会外界的出牌方式,他只按自己的方式出牌,也并不理会外界将如何接招!理论家们实在是把他想象得太复杂了,其实林墉自己却反倒简单:什么时候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十几年来,画了些人体画。只想到这是少人问津的所在,倒不是想在此范畴逞能。”(《马跑着,那是我》)紧跟形势无疑是一种智慧,但无视形势不能不说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智慧,尤其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说,林墉的单纯之处正在这里,而他的精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心无旁骛,尊重自己的初衷。众所周知,林墉其实是一位可以熟练操纵任何绘画技巧的艺术家,他的表现空间是非常广宽的,从巨幅革命历史画的“笔墨加素描”的厚重效果尝试,到访巴、访印作品的粗笔亮色狂扫,表现异国风情,再到人物写生的细腻个性刻划;从对墨韵、色彩的锐敏感受,到对各种画面气氛的恰到好处的营造,应该说均到了熟捻于心、得心应手的境界(因此,坊间有人戏称,正是才能的过于全面限制了林墉成为大师的可能。此说暂且存疑,留待后人证实)。如前所及,林墉是一位极为清醒的艺术家,因此,他每个时期的创作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与技法设定(当然只是相对的,绝对清晰的设定在艺术创作中根本不存在),对他来说,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就是不断为自己设定一个难度,然而消除这个难度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是独立于思潮和他人的好恶之外的。正如他所说的:“画家的一生,都在艺术实践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并在研究传统、寻找共性的同时,力求把个性完美地揉合在一起。每张画都是个性的一面,很多画合起来,就是完整的性格”。(《艺术扎记》)
也许正是为了塑造这完整的性格,林墉在1999年病后,创作了一批令众人大为惊异的山水画。这批山水画的面世有如林墉的身体状况一样,成为广东美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一时间引起了种种争议和猜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大彻大悟”说,“不能画具象”说,言之凿凿。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未必全无道理,而林墉自己的说法是:一直都对山水画心向往之,但却敬畏有加,不敢轻率下笔。本打算把山水画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再来圆梦,但突然间感觉来了,便放手画将下去(谈话大意)。笔者前年夏天拜访林墉时,他不厌其烦地把几十件作品逐幅张挂上墙,一边谈他的心得体会,由此可见其对这批画是颇为自得的。我注意到林墉在谈话中反复提到一个“气”字,由画而道,由道而佛,言语间颇具禅意。我在听着,思绪却早已被画面所占据:圆融苍莽的笔墨肌理,着实把他原来所建立的整个审美架构打了个粉碎——美仑美奂的造型没有了,精准爽利的线条不见了,唯见满纸云烟,笔走龙蛇,云山雾水,恍兮惚兮!据林墉本人讲,他对宾虹老人一直以来崇敬备至,对黄氏的笔法墨法更觉五体投地,对其中充澎的气感以及深藏的禅意颇有感触,于是不避形似之嫌,放胆效法。我倒觉得,与其说林墉希望以这种方式探寻山水之间的堂奥,一圆多年来欲言还休的山水之梦,倒不如说他其实是冀望于借用黄氏山水的外形切入一个新鲜的笔墨场景,以激活起新一轮的创造热情,并以此排遣身体的病痛带来的精神郁闷。比较林墉的“美人头”和后期山水画,有人可能会惊诧于画路的截然不同和趣味的南辕北辙,但我却惊诧于一位艺术家活跃的艺术触觉、不息的表现欲望和宽广的艺术包容度。林墉的几类作品虽然意旨不同,而宗旨却是不变的,那就是“穷尽物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手法,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外相不同,理却无异。释伽师说:不应着相。然而若未知相,焉知相为何物?不知相为何物,又焉知如何不着相?回到正题,“美人头”也罢,粗头乱服也罢,皆是外在形式(外相)而已。心之所系,方为根本。同理,“赞誉”也好,“非议”也好,亦皆为一时一局一枝一叶之评判,若观一叶而妄言一树,正如盲人摸象,实失之于偏颇。诚然,观众之于艺术家,有如水之于鱼,若无水,鱼之焉存?鱼儿固须知水,然则水又焉可不知鱼儿?度量一位艺术家的成就,须以无偏无执之心对之,这是艺术欣赏者和评论者应具的智慧。反之,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生涯,是一个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一个逐步展示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历练的过程。套用一句老话:赞誉和非议正如一把双刃剑的两边,互为矛盾、互为依存。真正的艺术家应忘掉双刃,着意剑端,直指本心,方能问心无愧,得证大道。这正是我们对那些忠实于自我、宠辱不惊的艺术家怀有深深敬意的原因之所在,也是林墉先生的艺术智慧及人生智慧对于后学者的宝贵启示。在此,愿借曾文正公诗一首作结: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生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2003年3月于羊石赤岗癸戊丁甲斋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 中国广州·三和轩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http://www.sanhx.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22号 信息产业部网站备案许可证:粤ICP备 0912875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