屐笠抛残越二年,江南塞北影如烟。
雪鸿笑我游踪减,末了湖山末了缘。
温泉水滑欣初试,好把尘襟细濯之。
野蕲杂陈供一饱,更从飞瀑觅新诗。
这是广东画家止庐黄少强(1901-1942)作于1936年秋的一首题画诗。籍由广东美术馆举办于2000年的《走向民间》黄少强作品展的机会、由广州美术学院李伟铭教授主持展开的对于黄少强文史资料的集中发掘和研究中,年谱汇编表明从黄少强1931年三十一岁直至他去世的1942年这十年间,他在全国各地广泛游历,与他担任南海小江敦睦小学校长(1927年)的那一段时期相比,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是奔波和动荡的,而且几乎没有长时间地在广东逗留。
但凡是艺术家,至少是为我们所熟悉的画家,在他的创作技巧积累到一定基础上的时候往往总是会有一个壮行千里或者是面壁十年的素材积累过程,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律。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但凡经过这样游历或者沉思,或者诸如此类、超越专业的精神探索阶段的画家,其创作水平的突飞猛进往往令人惊喜。这样看来,将这种负笈壮行、搁笔深思的过程或者是闪米特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小教派信徒,将某种特定的精神朝圣看作是终其一生的抱负或理想,乃至于人生的终极目的之所在,而朝圣者本人也籍由这种仪式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人生的升华和精神的纯净。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刘文东。自从我南下广东求学至今已近十年寒暑,在我的印象之中每年至少有两次,文东会前往全国各地游历。每次回来的时候风尘仆仆,卷带着一大堆的写生、速写的作品。因为舟车劳顿而显出的疲态中带着喜形于色,也相当能感染人。与一般人游历喜欢选择名山大川所不同的是,文东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游无定所。三山五岳之外,一些不为大多数人熟悉、甚至完全是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幽深溪谷也留下了他徜徉留连的足迹。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刘文东。
这恐怕涉及到了一种艺术题材的选择问题,已经不能仅仅单纯地看成是旅游路线安排的个人好恶而已了。早就说过,文东的游历写生如同著文,妙手偶得。一如柳河东《小石城山记》中说过:“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自然的美景无所不在,而不仅仅是名山大川才有。刻意地在笔下追求名山遍睹,可能会推动艺术原本的自由潇洒精神,而为名实所累。与其如此,那会不会还是随遇而安,信手拈来比较好呢?这种随意和潇洒给人带来另一层面的深思则是,文东所偏好描绘的冷僻小景可以说是对时人动辄三山五岳,江湖万里的那种如火如荼的热切场面的一种冷静补白。
我喜爱“补白”这个词。边缘的题材、边缘的游历路线给人以一种别出心裁的巧妙感。而位置的边缘化也给人营造了一种冷静思索的环境。
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个话题上来。即是一位作者在其一生中总要经历非此即彼的一种精神朝圣的过程,我们将它看作是艺术家创作生命的升华。反之,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阶段,无论这位艺术家多么优秀和才华横溢,到头来恐怕都很难不留下口实。我们来看看徐悲鸿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1948年)一文中所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画面上所见,无非董其昌、王石谷一类浅见寡闻从未见过崇山峻岭而闭门一画了一辈子(董、王偕年过八十)的人造自来山水!”徐在另外两篇文章之中,表述就更加不留情面。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不无过激的言论,但是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这里恐怕牵扯到了一个中国画家该如何画的问题。虽然宗炳在《画山水序》里提出要讲究“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称巧”;王微在《叙画》中也说过“本乎形者融”,看起来绘画的原本意义似乎是写生,可是自东坡以降,文人盲目信奉“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绘画的精神加工和写实基础被分离开来了。然后一直演变为崇尚写意而贬低写形,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精神发展脉络的。
例如说1704年,吴渔山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描述中西绘画的差异,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用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看得出吴在这里的描述还仅限于双方的实际区别,可谓比较客观。可是到了清代邹一桂论西画的时候说“虽然亦匠,故不入画品”,显然已经有了鲜明的定性结论了。
现代中国画的改革针对了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顽固特点,这对于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绘画严重脱离现实的情况而言是一种补救。广州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一方面秉承徐悲鸿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二高一陈岭南画派的直接延续,这种学术谱系的状况构成了文东艺术探索的基础。
艺术是具有现实基础的,意和逸不是同一个字,它们之间的概念不应当重叠。
文东作画,上学黎雄才教授,并从黄宾虹的作品种汲取养分。在文东的画面上,既有岭南画派的严谨,又有黄宾虹作品的烟云潇洒,可谓二者的融洽结合。而这种结合的最佳切入点,也可以说是文东千里迢迢历浙皖陕甘,足迹遍布江南塞北的旅途之中,一点一点地跟随前人游历的脚步、跟随前人的心路历程而摸索出来的。
2003年以后学业暂告一段落,我告别了五岭的烟云,回到了散雨飞花的江南,隐居在杭州运河畔的十里深巷之中。2003年和2004年,文东数次来杭州探望。每来杭州,与我游山玩水,披图衔觞,乐不思蜀,现在想起来都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文东数次向我提及,每每从杭州回家,甚至还在杭州的旅程中,他就不可抑制地产生一种强烈地想作画的欲望。甚至是在山中的古泉,甚至是在湖畔的小径,他告诉我说,他当时恨不得马上找一块卧石,铺开纸笔立即挥毫,痛写胸中之浩气。
我相信他的话,我想假如不是因为我这个旁人大煞风景的在场,文东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取出随身的纸笔,解衣般礴,枕石听泉,在山林傍晚愈来愈昏暗的光线和愈来愈清凉的香气中,奋笔疾书地挥毫、悠然自得地长啸。
一种精神朝圣者的心态。我微笑着,不易觉察的摇了摇头,很觉文东走火入魔。
在一个朝圣旅途之中的孤独行者,他能意识到天地比自己更大,历史比人生更久远;世界其实很辽阔,生命其实很悠长。面对在历史长河的雄浑波涛之中的那些被尘封了的回忆,坦然者比迷茫则更容易贴近永恒,虔诚者比玩世者更容易接近神秘的真髓。至此我突然想起我师李伟铭教授在散文《二闲集》中说过的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会估计到一个独立行走者孤寂的心态,这就正像我们无法估量释迦牟尼舍家出走的真正内心一样。莫高窟,鸣沙山,三危山,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和这里的夕阳、残塔之于南方闹市的广州就像遥不可及的彼岸,我从那里来,我还必须回去。”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文东多年前第一次来杭的情景,我由是而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回忆往事。——他住在我家隔壁的一家破旧的旅馆。安顿下来以后,文东即提出要拜偈黄宾虹先生的陵墓。黄宾虹葬于杭州玉皇山西麓的偏僻山谷墓地之中,我与文东在山下酒肆寻得一醉,冒着斜风细雨,寻径来到大师墓前。墓木已拱,荒草萋萋。谁能想到黄宾虹先生的作品对于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惊天动地,在艺术品市场上价值连城,而他的长眠之所会是这样的寂寥和凄凉呢?
我与文东扫尽墓前浮土,理清墓上枯枝败叶,久久矗立墓前,抚摩孤松,不忍离去。喜欢参观黄宾虹画展的肯定有很多人,可是愿意来拜祭黄宾虹先生陵墓的有多少呢?好学黄宾虹大师画法,从中汲取养分的画家肯定不在少数,可是千里迢迢赶来,在本来就不充裕的旅途里挤出时间,长久静静站立在大师埋骨之地的石碑前一言不发、默默思索者,有多少呢?
“未见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也。”
东坡在《文同传》里的这句话说得真好。
偏僻山谷里寂静而清寥的、适宜于沉思的上午时分,山谷里的雾气涌来,遮掩了远方都市千楼万宇的浮躁与喧哗。这个山谷以外的天下、那人生,变得好像梦幻泡影般地模糊不清。世界仿佛只剩下了这个暮气氤氲的山路,和两个在路上躅躅而行的路人。人一走,前面的雾就退,后面的雾就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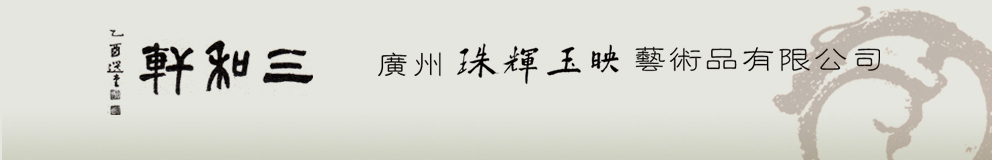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